仁礼关系与仁的形而上学结构及其思想史意义
来源:《东岳论丛》
2017-09-06 17:28:09
作者:杨晓伟
在孔子身后的儒家思想系统中,仁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其核心意义一直都是较为明确的,因而也是相对容易把握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仁所指的无非就是一种可以用仁爱或仁慈这类词语来解释的某种内在的道德情感,或基于这一道德情感而被观念化的特定德性。然而在孔子那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孔子是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谈论仁的问题的;在这些意义中,仁有时指的或者就是一种特定德性,有时指的则是一种道德原则,有时甚至是以其传统的意义而指称一种无关乎道德、而与教养有关的高贵仪态。而在他的全部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东西则是,在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意义上,他在仁与礼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关联,并将这一关联看作是仁的本质规定。在这一主导意义上,仁已经成了与其他意义迥然不同、但却更为根本的东西。不论怎样,至少表面看来,人们之所以直到今天也无法确切回答在孔子思想中仁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由于意义的多重性为人们的理解和把握带来的巨大困难。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尽管仁在孔子那里具有意指不同东西的多重意义,但这些意义就其自身而言却是相对明确的。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几乎从来也没有试图去澄清仁在这些不同的意义中指涉的是什么,以及这些意义之间可能具有怎样的关系,相反,却以一种不求甚解的态度自作聪明地将这些指涉着不同东西的意义看作是对同一事物的多方喻说;很少有人明白,这只有在仁的诸多意义在逻辑上具有一种内在统一性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意义事实上意指着根本不同的东西,因而它们之间并不具有这种内在的统一性,而且也不必具有这种内在统一性。
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仁在孔子那里的这种多义性理解为仁之内涵的丰富性,并以此来为孔子之仁在解释史中的这种意义含糊状态辩护,因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由于仁的多重意义之间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因此,具有多重意义这一外部事实本身并不构成仁之内涵的丰富性;如果满足于就此外部事实来赞叹仁之不可穷竭的丰富性,将会遮蔽孔子思想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事实上,为仁礼关系所规定的那一主导意义上的仁,恰恰由于这一本质性的内在规定,其本身就真正具有一种有待澄清的思想丰富性。尽管孔子本人无意于对这一在其全部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的仁进行系统的哲学分析,并由此构建一种道德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意义上的仁具有一种有待从道德哲学问题着眼来梳理的复杂的内在结构。而由于这一意义上的仁在孔子思想中的主导性意义,这种梳理其实对有效把握孔子的整个思想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尽管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仁礼关系在孔子之仁中的核心意义,但由于在后世儒家对仁这个重要的思想观念的阐发中很少有人真正理会这一决定性要素,因而这一意义上的仁其实一直就是专属于孔子本人的,并且因此也一直没有在其内在结构方面得到有效的澄清。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海外汉学家开始关注仁礼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所做的,大多只是引经据典地将这两者的关系陈列出来,而很少有人力图着眼于这一关系来确定为这一关系所规定的仁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究竟具有怎样的存在结构,并由此在这一根本意义上的仁与其他意义上的仁之间做出有效的区分。于是,孔子之仁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依然还是暧昧不明的,与之相关的许多重要的道德哲学问题就依然是难以理解的。
在现代,人们常常抱怨说孔子没有给予仁一个穷竭性的定义;这种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赞叹的抱怨一直都是人们任由仁的意义的这种含糊不清状态持续下去的重要理由。就孔子而言,在他回答弟子之问的各种场景中,他的回答的确很少是定义性的。然而很少不等于没有。他对颜渊的回答就是定义性的;而正是在这唯一的定义性的回答中,仁就是为其与礼的内在关联所规定的:“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然而另一方面,尽管孔子的回答是明确的,但它的意义、尤其是仁与礼之间的这种事关仁之为仁的本质的内在关联,并不容易理解和把握。直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萧公权还把这一关联理解为一种外在关系。在他那里,仁亦不过就是仁爱之德性而已,是作为殷商后裔的孔子借鉴殷商政治之宽和而发明出来以调和周礼之繁琐严苛的东西:“于殷政宽简之中,发明一仁爱原则,乃以合之周礼,而成一体用兼具之系统。于是,从周之主张始得一深远之意义,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之最后归宿与目的亦于是成立。此最后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于殷道者而创设,故仁言始盛于孔门。……以其为道正足以矫正周人礼烦政苛之倾向。”[1]
尽管颇为正确地把由仁礼关系来规定的仁看作是“最后目的之仁”,但在这段话中,萧公权显然是把这种关系当作一种外部关系来处理的。对他来说,仁是用来与礼相调和的东西。然而在《论语》中,仁却关乎礼在个人行为中的有效贯彻:“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相应地,从“克己复礼”这一本质规定来看,礼在个人行为中的有效贯彻对仁之所以为仁来说也是决定性的。
暂且撇开所谓的礼究竟包含着多少复杂内容这一点不论,无论如何,礼总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社会的秩序。就孔子而言,尽管他对周礼多有称美之言,但那只是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周礼在他看来相对较为完备适度,尽管其并非没有可以改进之处。而从“吾其为东周”(《论语·子罕》)这种话来看,对孔子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夏礼、商礼或周礼,而是礼本身所意味着的东西,即让社会处于稳定状态的秩序。就像各种特定的德性乃是具有各自的客观价值的善一样,秩序也同样是一种具有其自身客观价值的善,只是这种善是属于社会的。就其力图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建秩序这一点而言,孔子真正在意的其实就是这种有别于个人德性之善的社会之善的实现,而就其自身的存在规定而言,仁作为一种纯粹个人性的东西,构成了实现这种社会之善的基本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仁礼关系所规定的这种根本意义上的仁,就成了与某种特定德性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必须明白,作为仁爱之德性的仁仅仅是一种被观念化了的内在的道德情感,因而在其自身内部并不包含有它与礼的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作为这样一种具有善的价值的东西,其本身还需要在某种行为中获得自我实现,因而根本就不会成为为礼所表达的秩序之善的实现提供基本可能性的东西;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孔子之仁的诸多意义中,似乎也有仁爱之德性这一层意义;至少在回答樊迟之问时所说的“爱人”(《论语·颜渊》)便与仁爱这一德性相关。但是严格地说,“爱人”并非是仁爱之德性,而是这一具有善的价值的德性在个人行为中的具体现实化,是其价值的实现。因此,即便在“爱人”这个特定语境中,仁指的也不是某种特定的德性之善,而乃是这种德性之善在其中实现自身的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在哲学层面上,孔子似乎并不关心“何者为最高的善”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相反,他那以仁为主导词的思想所关心的乃是各种善的自我实现问题。而由于他更在意的不是个人的灵魂得救,而是政治世界的稳定有序,因此,较之于个人性的德性之善,他的思想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秩序之善的实现方面。他对仁的定义性的说明就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孔子的全部思想中,与其一直拒绝为人性做出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规定这一点相适应,他几乎从来也没有试图通过将某种特定的德性之善确定为一种基本的人性规定并给予其形而上学的论证,从而在哲学层面将其确认为某种是为人类意志之最终目的的最高的善。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对这种被他称作是质料伦理学和目的论伦理学的思想的严厉拒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教训。
康德之所以拒绝这种伦理学,其原因在于,在这种伦理学中,人们不是从一个先在的实践法则中推导出善的概念,而是把某种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经验性东西作为人的意志所欲求的善的质料(客体),作为意志进行决断的先决条件,并力图由此推导出实践法则。然而事实却是,这种经验性的、作为欲求质料(客体)的善是以快乐与否的主观感受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与人们的主观偏好有关的。因此,在这种伦理学中,作为意志决断之依据的,就不是理性自身的形式化的、因而也就是无关乎经验性欲求客体的先天法则,而乃是对作为经验性欲求客体的善的表象以及主体与这个经验客体的关系。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意志的道德决断中,它实际上是听命于它的经验性的主观偏好的,因而是他律的,而道德本质就在于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以及合乎这些法则的职责的独一无二的原则。”[2]
对这里的问题更具借鉴意义的是马克斯·舍勒的相关说法,即:作为欲求客体的善的价值只能是非道德性的,因为真正道德意义上的善,其价值乃是一种人格价值;只有人格才真正承载着道德性的善与恶的价值,具有最终区分这些价值的质性并将其作为可能的趋向而在人格行为中实现它们的能力。而如果仁爱之德性是一种道德性的善的话,那么这种善的价值就只能存在于实现着它的人格行为中,并且恰恰因此而永远也无法真正作为一种欲求客体或质料在实现着它的行为中被意指;也就是说,它根本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欲求的对象性客体,除非人们仅仅将这种德性看作是一种无关乎善的价值的、概念化的人格特征。换句话说,只要人们将仁爱或者其他什么德性之善看作是意志的欲求客体,那就无可避免地意味着这种德性之善与规定了其所以为善的价值割裂开来并仅仅成为一种概念化的人格特征或标志。而这样一来,伪善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完全可以为了看起来是善的而利用这些标志。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的,“每一种试图在价值本身的领域之外为比方说善与恶设置某种公共标志的做法,都不仅会在理论上导致认识错误,而且还会导致最为严重的道德欺骗。在这种做法中,人们每每错误地以为善或恶是与这样一种存在于价值领域本身之外的记号——不论这记号是人的一些身体或心灵的气质和特征,还是一个阶层或团体的成员资格——联结在一起的,并且据此来谈论‘善与公正’或‘恶与不公正’,就像是在谈论一种可以客观地规定和定义的种类一样,这时,人们就必然会沉溺于某种法利赛式的伪善中,这种伪善把善的可能载体以及它们的公共标志(作为纯粹载体)看作是相关的价值本身,看作是价值的本质,但它们对价值来说却只是作为载体而起作用。”[3]
就孔子而言,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孔子的仁的思想所关注的始终是各种善的价值的实现,正如前面所说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将仁作为一种特定德性以便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将这一意义上的仁确立为某种人性规定;然而这却是后世儒家思想家们在仁的问题上唯一关心的事情。也恰恰是因为如此,在他们的思想中,仁几乎总是不由自主地变成用以标明人性之善的标志物,而中国古代的道德虚伪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可以对仁爱之德进行某种客观的分析以确定其在各种道德之善的价值中的等级结构,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孔子所关心的事情。不论人们可以将仁爱之德的善的价值等级定得有多高,仁在孔子那里也不是这种价值本身,而乃是这种价值在其中得到自我实现的东西。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孔子思想比之后世儒家要朴实得多。他从不像后者那样动辄就搞出某种浮夸不实的道德境界以高自标榜;他的仁是极为平实的:“仁远乎载?我欲仁,仁斯至矣。”(《论语·述而》)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愿意以仁的方式行事时,他就处于仁的状态。
二
孔子之仕朴实无华,但这个平实无华的仁却是不容易理解的。一般而言,仁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东西,事关人格的塑造和完善,因而是纯粹个人性的。然而在孔子所提供的定义中,这个纯粹个人性的仁却在自身中本质性地涉及到作为一种完全非个人的、并且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礼的有效贯彻,涉及到外在的秩序之善的实现。而这就意味着,在孔子那里,个人人格的完善,不仅涉及到诸如仁爱之类的个人性的德性之善的实现,而且还本质性地涉及到秩序之善的实现,而且对孔子来说,后者才是仁的规定性要素。这一点具有极为深刻的哲学意义,后面将会对其做出专门的讨论。在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仁礼关系由此而不可能是现代解释史上的那种颇为流行的内-外关系,即:礼是外部存在,而仁则是让礼具有精神内涵的内在之物。相反,对孔子来说,仁并非是用于丰富礼的精神内涵的内在之物,而是在自身中包含着让礼的贯彻亦即秩序之善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一内在要求。
为了抵制在仁礼关系问题上的这种内-外之分,芬格莱特认为,仁与礼都是一种外在行为,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礼’指符合其社会身份的特定行为,这种行为是恒常准则的榜样;‘仁’则指表达个人取向的行为,表示他对于‘礼’所规定的行为的服膺。”[4]芬格莱特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他混淆了作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的礼与循礼而行的行为。另一方面,他忽视了,特定生活情境中具有个人取向的行为,只要它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就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语境中的行为,而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道德规范自有其来自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的约束力。如果人们只是由于屈服于这些外部力量而服膺礼法,那么,这种服膺本身就不具有任何道德性,因为在这种服膺中,行为的核心是一种他律原则,而道德的本质就是自律。相应地,只要仁还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它就应当建立在自律原则上。孔子自己也明确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因此,只有当这种服膺是出于个人意志的自主选择的时候,它才具有道德性。其实,即便就仁礼关系是仁的内在规定这一点而言,也不能把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循礼而行这件事本身理解为仁,相反,在这一特定意义上,仁指的是个人对循礼而行这种行为方式的自主选择,尤其是对诸多可能还相互冲突的礼制规定在各种具体生活情境中的适用性做出某种反思性的自主决断。这一点乃是礼之得到有效贯彻的一个存在于个人方面的最基本的前提;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仁作为纯粹个人性的东西乃本质性地在自身中包含着它与礼的一种内在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史华兹对仁的说明倒是说中了某种东西。他认为,仁指的是“个人的内在道德生活,这种生活包含有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的能力”。[5]
真正说来,不是个人性的道德生活包含着反思能力,而是,反思乃是个人道德生活的存在本质和基本标志。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正是在意志以其自身为对象的反思中,人才真正进入道德层面,并由此而成为具有道德能力且对其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的行为主体。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反思就是意志以其自身为对象的主观性和内在性,因而只有在反思中,意志才是自由意志,才真正是其本身。从孔子这方面说,之所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正是由于在仁的意义内涵中包含着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生活的反思。同样的,反思也构成“为仁由己”内在基础;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对循礼而行这一行为方式的自主选择中贯穿着纯粹个人性的道德生活即反思。可以说,正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道德生活,乃为作为一种外部存在的礼在个人行为中的贯彻提供了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基本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在孔子那里,不仅在整体上选择循礼而行这件事情本身,而且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对诸多礼法规范的适用性的自主选择,也必须为这种反思所贯通。这一点构成了孔子与那些基于人性的形而上学预设来谈论所谓心性的后世儒家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孟子最先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讨论人性问题。他将经验性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概括为仁义礼智四端,并将其提升为人性的形而上学规定以及人性之善的标志性特征。而依据这一人性规定,理论上说,人们让潜藏在人性中的这所谓四端得到自然的发展,就可以充分实现其人之为人的良善本性。与此相应,正是通过将人的知性能力即所谓的心看作是承载着这些良善本性的主体——朱子在解释尽心知性时说所谓的性乃是“心之所具之理”(《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是符合孟子的意图的,——孟子乃可以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这句著名的话语充分表明了,孟子抱持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人们可以直觉性地、因而就是非反思地从整体上把握住善,并将其作为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具体生活情境的东西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因此,尽管他说过诸如“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之类的话,但其目的不过是告诫人们不要囿于耳目之知,为外物所蔽,而应立乎本心并与之保持一致。这里如果还说得上道德的反思和选择的话,也只是涉及到是殉于耳目之知为外物所蔽还是立乎本心。因而有意思的是,由于包含着四种标志性特征的良善本性乃是所谓的“心之理”,而心实为这种良善本性的主体,并且由于由此而有的良知良能,这种貌似反思的立乎本心恰恰意味着在具体生活情境中是无须乎反思和选择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恰恰可以非反思地、直觉性地从整体上把握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非反思的直觉中把握到的善,由于其非历史的、抽象的整体性特征而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具体生活情境,而这一点则保证了,将这种直觉性的善的知识转化为具体行为时也是无须反思的,同时也保证了,这些行为本身具有一种完全无条件的善的价值。所谓“集义”和“养浩然之气”的前提就在于此。
与此相反,对孔子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打算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从形而上学层面讨论人性之善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些话表明,对他来说,人性是可塑造的,因而是历史性的。因此,如果说按照孟子的性善原则,则极端的社会状况会摧毁人性,那么对孔子来说就可能会这样:人之所为的一切都是人性的,都是带有人性特征的;有什么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性。而与这一关于人性问题的基本思想态度相适应,孔子并不承认某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之善;他从来也没有以这种方式谈论过善。相反,从《论语》中人们自然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凡是道德意义上的善都与具体生活情境中的反思性的选择有关。因此,在孟子那里根本不会成为问题的东西,在孔子那里却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论语》的一段话是颇可玩味的:“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儿子告发父亲偷羊,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讲是可以作正直公正看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中,正直公正却是与在孔子看来更重要的德性即孝慈相对立的。因此,他并不认可叶公的判断。相反,他选择的是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并因为这更合乎人情、符合人性而认为这种选择同样包含着某种正直。
这个故事触及到一个基本的道德事实,那就是,尽管各种美德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但是,它们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自我实现却是受情境规定的,因而是有条件的,因为它们之间常常或是天然地、或是由于具体情形的缘故而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比方说,慷慨大方和勤俭节约都是美德,但是它们之间却是紧张的,因而它们是在行为中实现其善的价值还是转而成为一种恶,取决于具体的情境规定以及对其适用性的选择是否恰当;同样的,正直也是一种美德,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正直会转而成为极不厚道的残忍;还有,忠于职守是一种美德,但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长官艾希曼,以及最后一个开枪射杀试图翻越柏林墙逃亡西德者的那个东德警察,他们的忠于职守却是一种赤裸裸的恶。由此可见,在没有反思以及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道德决断的情形下不加选择地盲目服从某些道德原则是很危险的。因此,只有通过真正的反思来确定在特定生活情境中适用何种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何种德性,它们才能真正在其自我实现中让行为本身成为善的行为,而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在真正的道德反思中人们才能恰当地确定在具体情境中何者为善。
毫无疑问,孔子是清楚这一点的,也只有这样,他才看重这种道德反思能力,并极为鄙视那些没有反思能力并盲目行动的人:“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就此而言,他大约不会认可孟子基于人之性善这一形而上学预设以及心性关系而提出的对善的那种整体性的直觉把握。而由于形式性的礼法制度永远也无法涵盖无限多样的具体生活情境,并且诸多礼制规定之间同样也会存在着紧张关系,因而,这种反思性的选择不仅对于个人德性之善的实现是必要的,对于礼在个人行为中有效贯彻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而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本质的深刻洞察,他比后世儒家更在意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如何运用道德反思能力在具体情境中就诸多礼法规范和道德原则的适用性做出选择。而再详尽的礼制规定也无法做到全覆盖的具体生活情景的无限多样性则使这种反思性的道德选择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事情。孔子自己就说过,“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三
作为纯粹个人性的道德生活的反思乃是上述这些道德选择的最终基础,但只要仁在自身中包含着这种选择,那它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粹主观内在的道德生活;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包含着客观伦理层面的东西,即便就其自身而言,仁终究是个人性的。这里的问题是,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就礼法制度的诸多具体规定的适用性进行道德选择,这件事情的一个结构性前提就是,个体意志已经在一种总体性的道德决断中决定循礼而行,而这也就意味着从整体上接受由礼制规定为善的客观内容和规定,并由此而接受它的约束。“克己复礼为仁”这个说法本身就表明,这其实就是仁的本质规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表面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结构特征,那就是,在纯粹个人性的东西的内部包含着完全非个人的客观存在作为其自身的原则。这里的矛盾在于,不管怎样,道德生活的存在论前提就是意志自由,而且也正是基于这一自由,仁才是可能的,而礼作为非个人的、外在的、且对个体意志具有约束力的东西是与这种自由格格不入的。
但是,表面上矛盾的事情却未必不具有其存在论上的合理性。人们必须明白,自由作为意志的本质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的任性;听命于个人意志的自然冲动,恰恰意味着不自由或伪自由。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的一段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那里,黑格尔把国家政治权力以及法律制度、社会风尚等等客观存在看作是伦理的实体存在,并由于这些东西源自普遍意志而将其看作是对个人的特殊意志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有所约束的义务只是对无规定的主观性或抽象的自由、对自然意志的冲动或出于自己的任性来规定其无规定之善的道德意志的冲动来说,才会显得是一种限制。但是在义务中,个人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他摆脱了他处于赤裸裸的自然冲动中的那种依附状态,并且摆脱了他作为主观特殊性在对应为与可为之事进行道德反思时的那种沮丧状态;一方面则又摆脱了那种无规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行动的定在及客观规定性。在义务中,个人乃向着实质性的自由解放自己。”[6]
对于这里的问题来说,引人注目的是,道德意志的冲动也被黑格尔看作是妨碍真正自由的东西。而所谓道德意志的冲动指的是,个人意志固执于抽象的、没有具体的客观内容及规定作为原则的主观良心,完全无视政治-法律制度等客观的伦理实体的存在,将主观任意设想的特殊的善当作出自普遍意志的东西来贯彻。因此,这一切其实都与道德良心的存在结构相关,而由于黑格尔所揭示的道德良心的这一存在结构对于理解孔子之仁的内在结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所以,对之做一番简要的梳理还是有必要的。
关于良心,黑格尔说道,“真实的良心乃是欲求那个自在自为地就是善的东西的意向。”[6]这里的“善”并非通常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指个人的特殊意志与作为其本质的普遍意志或意志的概念的统一。个人的特殊意志如果固执于自身,那么它就将受制于意志的自然冲动,因而也就受制于外在的偶然事物;只有当其基于内在的道德反思而在其普遍本质中理解自身,从而以作为其存在本质的普遍意志的内在规定为自身原则的时候,亦即与普遍意志相统一的时候,才是真正自由的,才真正实现了其所以为意志的自由本质。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把善规定为“被实现了的自由”。[6]至于良心,它之所以是欲求善的意向,乃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体意志在其以意志本身为对象的自我反思中——在这种反思中,个体意志将自己确认为普遍意志的具体化存在,确认为在其具体定在中的意志——获得的一种自我确信,以至于,良心就是在其主观性中意志。正是由于这一点,作为在这一反思中自我确信,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的统一才必然会作为自由意志的实现、亦即作为意志的真正存在,成为良心、亦即纯粹主观性中的意志所欲求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就个人的特殊意志与之相统一的普遍意志而言,它之所以是普遍意志,之所以是意志的普遍本质,就在于,它是规定了所有的意志所以为意志的东西,是所有意志的共同本质。而这也就意味着,当个人的特殊意志在其中确认自身并因而欲求它与这一普遍意志相统一的时候,对个体意志来说,就必然会有诸如权利和义务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客观性的东西作为善的客观内容和具体规定,而作为欲求善的意向的良心也就必须以这些东西为原则。然而在严格区分道德的主观内在性和伦理的客观性的黑格尔那里,所有这些都只有当意志超出良心的这种纯粹的主观性而进入客观领域的时候才能得到实现。
在黑格尔那里,善的这些客观内容作为良心的原则和义务,它在伦理层面上是作为国家权力、法律,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风尚等等客观存在而出现的。黑格尔之所以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伦理的实体,乃是因为,它们出自普遍意志并表达了普遍意志,而国家作为普遍意志的现实化存在,作为这些东西的根源,则由于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真正超越他的特殊性并与普遍意志达到统一,而被黑格尔直接看作是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的统一,看作是“实体性意志的实现”。很明显,黑格尔没有像康德一派那样撇开国家-伦理层面的东西抽象地看待道德,因而也就没有像康德那样把意志自由局限在主观领域。他的设想的合理性在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解释学事实,即: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共同体以及相关的政治-社会系统,对于一个具体个人来说,乃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它为个人存在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可能视域,因而任何个人都只能在这个特定的先验存在中理解并塑造自己。这就意味着,个人的任何道德选择、任何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的个人性的道德判断都已经在一种存在论状态上受到前者的结构性制约;换言之,道德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不是任意的。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说法就是,“何者是善或不善、正义或不义的内涵,这对私人生活的通常情况来说,乃是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与风尚中被给出的。”[7]
当然,黑格尔所想的还不止这些。在他看来,由于良心本来就是个体意志在主观反思中于普遍意志面前的一种自我确认,因此,如果固执于意志的这种主观性,也就是说,如果固执于道德良心本身的这种没有客观原则的纯粹主观性而完全无视上述那些伦理实体,那么,其可能的结果之一就是,个体意志把自己的特殊性直接等同于他与之统一的普遍意志并在个人的意志行为中强行贯彻没有客观规定之约束的自身,而这其实也就是为所欲为、为非作歹的出发点。就道德行为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特殊的道德意志会把自己主观认定的特殊的善当作普遍的善来贯彻并以之要求所有的人。因此,黑格尔警告说,“作为形式的主观性的良心简直就是处于反转为恶的突变点上的东西。道德和恶在独自存在并独自知道和决定的自我确信中有其共同的根源”。[6]道德与恶具有共同的根源,这够震聋发聩的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黑格尔认为,人的道德判断必须超出良心的这种纯粹的主观性,接受法律制度、社会风尚等客观伦理实体的约束。在他看来,只有当政治-社会处于极端状态时,诉诸内在才是被允许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在其中,现实乃是一种空虚、无精神且无行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从现实生活遁入内在生活对个人来说才会是被允许的。”[6]
现在回到孔子的问题上来。在孔子那里,以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行为规范等等为基本内涵的礼作为一种客观的伦理实体,其对仁的意义内涵的结构性参与表明,在关于仁的构想中,孔子没有撇开客观伦理抽象地固执于道德生活的主观内在性,尽管这种纯粹个人性的道德生活本身也的确构成了仁的一种基础性内涵。因此,尽管表面看来,孔子对固守纯粹内在的个人道德生活这种做法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比方说对蘧伯玉的怀德自守就是如此:“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但是人们必须看到,孔子对这种向内心生活的遁入的赞赏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蘧伯玉所处的社会是一种全面而极端的无道状态。况且,孔子许之以君子,却并没有以“仁”许之。而这正是因为,仁包含着比纯粹内在的道德生活更多的东西。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句名言来看,孔子非常清楚,礼的根源是国家。是国家及其主权者创建这些东西并保护这些东西在其中真正具有效力的境域;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处境之法’(Situationsrecht),统治者整体性地创造并保护作为一个整体的处境。他拥有对这种决断的垄断权。国家主权的本质就在于此。”[8]对孔子来说,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政治学实质其实就是指国家主权者无法垄断这种决定权。
因此很清楚,在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构思中,有一个从来也没有被注意到的、但却实际存在的思想预设,那就是,国家或共同体的存在乃是仁的现实化的一个结构性前提,正如国家共同体在黑格尔那里是善的实现亦即意志自由的一个结构性前提一样。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国家具有它与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不同的另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道德:“国家的道德并非由个人自己的信念来支配的那种伦理的、反省的道德。”[7]在他看来,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它的自我维护,“国家没有比它的自我维护更高的义务”[9],因而也就不应站在一般个人性的道德意义上把国家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看作是不道德的。
从孔子方面看,他的很多话语表明,他很清楚国家政治同事关个人道德节操的道德行为之间的根本差别。比方说,尽管他批评管仲不知礼,但当他的弟子用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问题指责管仲的时候,孔子明确表示,他更看重管仲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成就:“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管仲之所为,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行为处理的是国家政治事务,属于国家权力的政治谋划;而这些事务与作为个人事务的仁,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前者属于公共领域,而后者则属于私人领域。就孔子而言,他的思想中固然不无将政治道德化的倾向,但他也实实在在地通过对管仲的政治行为的赞赏而充分肯定了国家政治及国家权力的政治谋划的存在合理性。不仅如此,他甚至将管仲的政治活动看作是大有仁爱之德的事情。之所以如此看待管仲的作为,并不是说孔子意在混淆政治事务与作为个人行为的仁之间的本质区别。“如其仁如其仁”这个说法的唯一合理解释是,管仲的政治活动有效地维护了一个政治社会的秩序,这个秩序在实际上不仅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同时也维护了仁的现实化的结构性前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诸如权利和义务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得到过制度上和法律上的确认,也没有在思想中得到确认,但另一方面,一个特定共同体及其内在秩序的有效维护,毕竟保证了个人超出他的特殊性而进入普遍性中的一个存在论前提。
不管怎样,通过对管仲的赞赏来肯定政治及国家权力的政治谋划,这一点在孔子那里是清楚明白的,以至于史华兹不无遗憾地认为孔子在国家政治问题上完全倒向了以国家权力的自我维护为最终指向的国家理性:“在这里,他似乎猛烈地朝‘国家理性’倾斜。”[5]另一方面,孔子对管仲的赞赏在中国古代政治道德主义传统中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看起来颇为怪异的是,作为儒家思想传统的开创者,孔子竟然是整个儒家思想史上唯一一位对管仲持肯定态度并加以赞赏的思想家。要知道,在仅仅把仁理解为某种特定的道德情感或特定德性的后世儒家传统中,那些道德境界高得吓人的思想家们对管仲是非常不屑的。在他们那里,政治是完全被道德化了;他们将政治化约为完全道德化的所谓“仁政”,但除了诉诸统治者或国家管理者的“仁爱之心”这类没有任何具体的客观内容的内在之物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相关制度化设想,以及任何有关国家为实现这一“仁政”目标所需要的实际政治运作模式的构想。至于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运作相关的一切属于国家政治的固有之物的东西,则更是完全不被承认的,而这只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不能为道德所涵盖。
总的说来,造成后世儒家与孔子之间的这种深刻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后世儒家学者们关于仁的思想中,仁仅仅是一种特定的德性,因而根本缺少孔子之仁所具有的两个至关重要基本维度,即作为真正个人道德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仁之所以为仁具有规定意义的仁礼关系。在后世儒家学者那里,本质上是内在的道德仅仅是一种直觉的、因而是非反思的东西。相反,在孔子那里,道德反思始终是一种结构性要素,而仁礼关系作为仁之为仁的本质规定,则对道德的这种主观内在性构成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限定,这一点又让仁所包含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主观内在的个人道德生活。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孔子的道德思想是极为平实而朴素的,因而人们很难在他那里看到常常出现在高谈心性之学并因而喜欢诉诸非反思的所谓“内在”的后世儒家学者身上的那种浮夸和偏执。刘子健曾在他的思想史名著《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经过两宋而完全转向了内在领域。转向内在的一个直接的思想方面的结果是,人们竞相用高得离谱的道德境界高自标榜,这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于是道德出现严重的虚伪化;与此同时,道德的不宽容与专制也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在政治道德主义的压制下变得完全没有地位;全面进入权力体制内的儒家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能力而只能诉诸道德,因而总是力图在公共政治领域中贯彻他们主观认可、因而被当作是普遍必然之物的道德之善以压制实际政治,以至于任何不顾及那些空疏迂阔的道德直面实际政治问题的政治举措都要受到道德非难,许多杰出的政治家还由此而被斥为“奸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的全面道德化也使国家权力及权力本身被道德化了,以至于统治者可以轻松地用漂亮的道德言辞来掩盖统治的残暴。因此,中国传统中的国家政治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什么“仁政”理想,从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相反,政治在道德言辞的掩盖下反而是日趋野蛮;与此相应,政治无能也成为转向内在后的中国政治的另一个基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想爆料?请登录《阳光连线》( http://minsheng.iqilu.com/)、拨打新闻热线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录齐鲁网官方微博(@齐鲁网)提供新闻线索。齐鲁网广告热线0531-81695052,诚邀合作伙伴。
把握新时代的三重维度
- 准确把握这一政治判断,是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新任务、新举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详细]
- 《学习时报》 2017-12-06
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论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
- 政党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政党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全球各类政党面临的一个共同命题。[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2-02
山东:让世界看到中华文化的光芒
- 几年来,山东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世界影响,也让世界舞台上的...[详细]
- 光明日报 2017-11-26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之武装全党,才能坚定全体党员信念,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作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详细]
- 《红旗文稿》 2017-11-26
努力开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就应更加坚定信心,直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的现实,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进一步努...[详细]
- 《红旗文稿》 2017-11-26
迈好“新时代的步伐”
- 攻下这些“娄山关”与“腊子口”,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既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更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迈好“新时代的步伐”。[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1-26
让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必由之路。[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1-18
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我们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理解、准确...[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1-11
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人民日报一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1-11
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经济工作
- 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1-10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广大党员干部、广大群众所掌握,必将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1-09
不忘初心:理解十九大精神的钥匙
- [详细]
- 光明日报 2017-11-08
共同创建文明有序的互联网群组空间
- [详细]
- 人民日报 2017-1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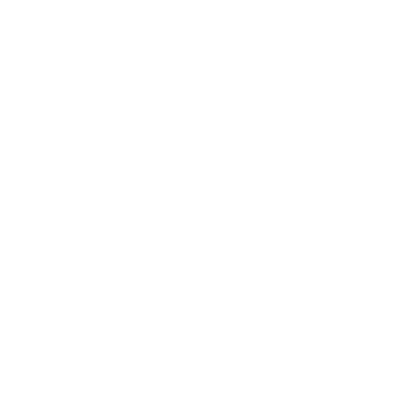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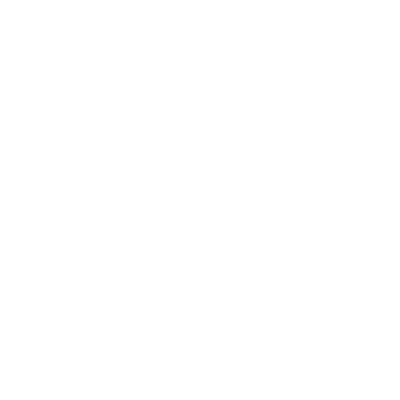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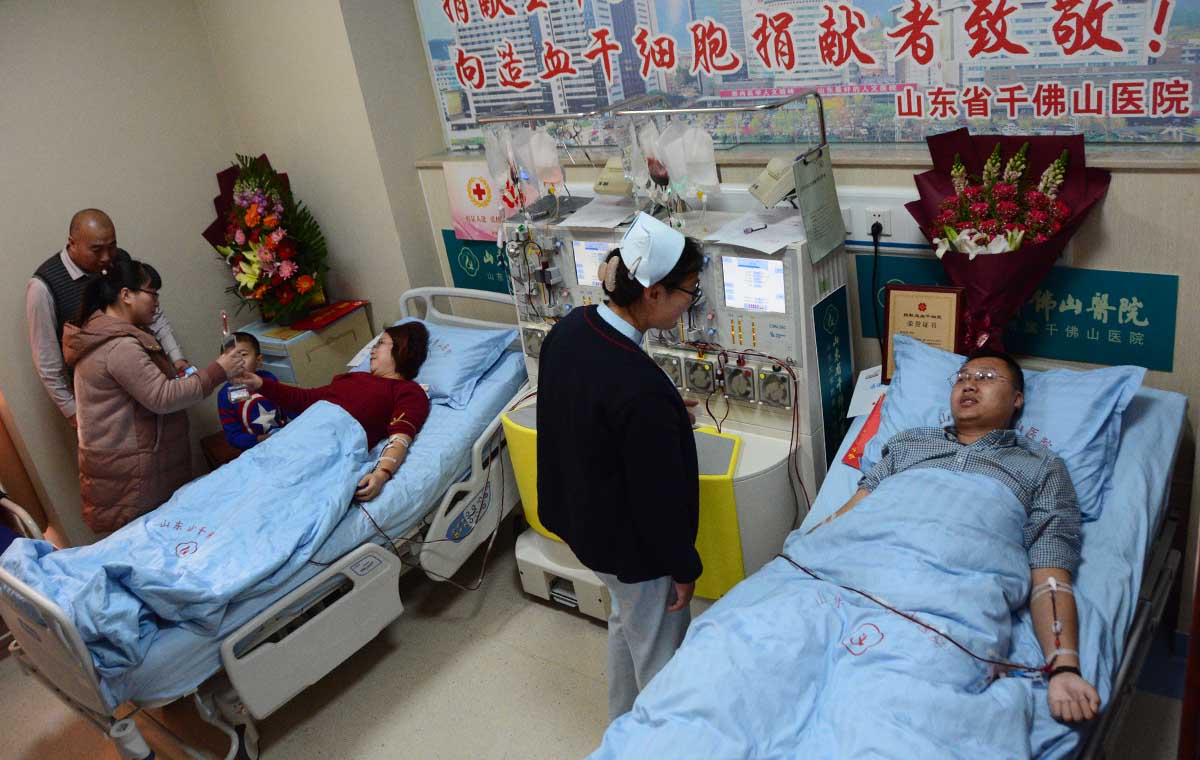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齐鲁网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我来说两句